界面新闻记者 |
界面新闻编辑 | 姜妍
十九岁的时候,张秋子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课上,听着老师一句一句念讲义,自己再把文学史知识一句一句抄录进笔记本。但相较于在课堂上的所得,她感觉课下自行阅读文本的时光,才被文学真正“点燃”或者“感召”。
如今的张秋子已经是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教师,她尝试带领学生精读文本,慢慢发现,文学并未锁闭在幽深的阁楼,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生命经验打开门缝,得到进入之的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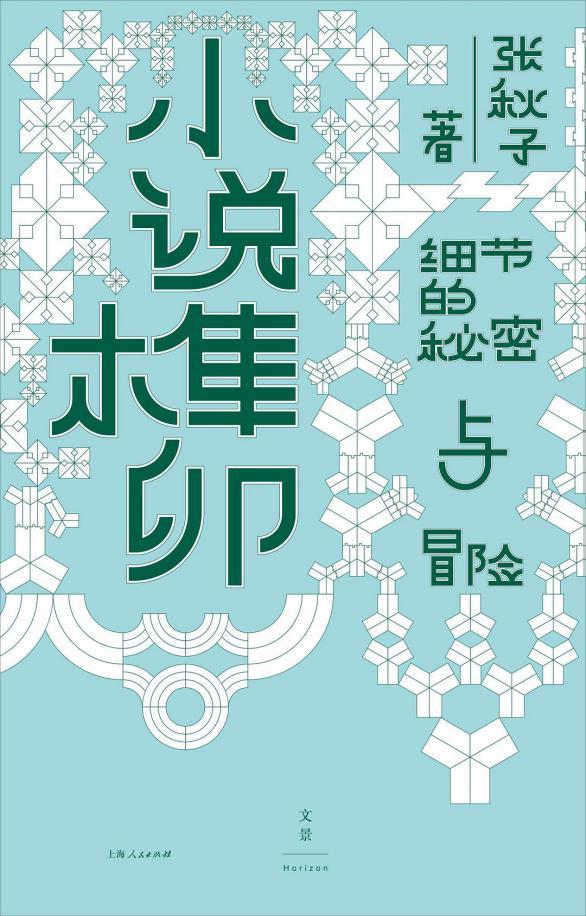
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 2025-8
“榫卯”,是一种特别的构件连接方式,榫与卯,看似彼此独立,却在咬合中形成坚固灵活的整体。19世纪的英国作家安东尼·特罗洛普用“榫卯”形容预埋的细节机关,每一个计划好的细节间,都是精密呼应的“榫头”与“卯眼”关系。
在新作《小说榫卯》中,张秋子借这一隐喻,引导读者以细节为支点,用巧力破解文学。习得这种“巧力”的读者,能够跳出单调、暴力的文学史叙述。在上海书展期间与界面文化的对谈中,张秋子分享了时下流行的女性主义批评方法,最近文学圈的鉴抄事件,以及当耐心与想象不断被日常挤压,我们还可以如何阅读文学。
意识形态化的角度很容易走向概念性的解释
界面文化:你在书中强调的是一种从“细节”着手的阅读方法,这和我们更熟悉的文学史课堂教学方法有什么区别?
张秋子:传统的教学方式有其重要性,会让我们在进入细节之前有一个整体性的概览。但问题在于这样的阅读方式离我们的世界太远、太抽象了。从细节着手的阅读,无需马上面面俱到地理解文本,而是抓一个和自己心心相印的小点爆破,再潜入到更广阔的文本水域中。这样的阅读方式能够让读者和文本有一种更亲密、更及物的接触,让人觉得文本不是一个与自身无关、遥远之物。
我的学生面对歌德的《浮士德》时一开始都特别恐惧。因为《浮士德》很长,又是诗体,人物众多,场景变化也多,阅读难度很高。后来有一个女生分享了一个小细节,是玛格雷特由于梅菲斯特的魔法爱上浮士德时,她用花瓣做占卜,判断浮士德是否爱她。这一桥段在今天的影视剧和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是很多见的。当这个女生分享出这一细节时,这个古老的、磅礴的文本和我学生们的生命更近了一步,形成了个人化的对话。

界面文化:和系统化的文学史知识相比,从细节生发的阅读让读者能更切身地和文本产生联系。在建立起这种关联之后,我们是否仍需抵达一种知识性的东西?
张秋子:当然,我们并不单纯是在这个小细节里徜徉一下,或者交换经验就结束了。不过我们最终的知识不是信息,或者说不是由文学史大纲构成的。实际上我们现在所学的文学史是很晚近的产物,它对于学院之外的人来说意义不大。
大众不需要知道谁继承了荷马的文学遗产,谁又受了但丁的影响,而只需要随机抓起一本书来读就行。读得多了自己的脑海中会自然形成一套理解文学传承和绵延的路径,而非依靠学院内文学课堂提供的单调的、甚至有些暴力色彩构建的脉络。
知识的本质不是由信息或者说知识材料构成,而是一种心智的结构。阅读能够培养一双站在一定距离之外、审视我们个人生活的眼睛。我有个学生去一个学校当语文老师,有一天在集体宿舍洗漱的时候,旁边的男生突然说了一句:我的生活完了,我从此就是一个语文男老师了。但我的学生观察到,当旁边的男生为自己的人生画下了一个终止符,洗衣服的水龙头的水还在流,那种不由分说的外在的生活仍然冷峻地、不动声色地前进着。

译林出版社 2025-2
他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观察,是因为我们共读过纪德的《背德者》。在这部小说的最后,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已经终结,其实小说就可以结束了,但是纪德加了神来一笔,最后写到一个女佣举着蜡烛推门进来。这让读者感受到当一切都终结为平白的灰色,生活本身还在往前走,这种张力就一下子就出来了。
界面文化:这种审视性眼光让人获得的是什么,它能够强化人对生活的幸福感吗?
张秋子:我不知道它是否一定导向幸福感,但是它会让人有一个置身事外的判断,而不是始终无意识地被生活的激流推着往前走。我想文学教会我们的其实是,我们并不需要每时每刻都赋予生活沉重的使命感。可能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有一个时刻能分身出来,跳出来回望,哪怕这种回望带着一些遗憾、惋惜和幽默,都是一种珍贵的、能够让我们识别自己生活意义的瞬间。
界面文化:但要求普通读者通过艰苦的努力,处理文学叙事中细节的“光晕”,是否太理想化了?
张秋子:是的,我并不强求所有人都按照这样的要求读文学,我认为我没有这样的权力。每个人的天赋、兴趣点、知识构成都不一样。我能做的只是通过分享我的兴趣,吸引一些本来就对这种阅读方式感兴趣的人。所以“启蒙”对我来说是一个危险的词汇,充满了自我陶醉的气息。
我最喜欢的理论家雅克・朗西埃在《无知的教师》中写到,作为老师,我们并不比学生知道的更多。我自己在上课的时候也经常感觉到,学生们欠缺的其实无非就是时间。如果他们多下苦功读个十来年,也可以像我一样找出这些文本细节。他们有的而我不必教的,是他们独一无二的经验。我也非常依赖他们的经验,他们丰富多元的经验启发着我文学解读的诸种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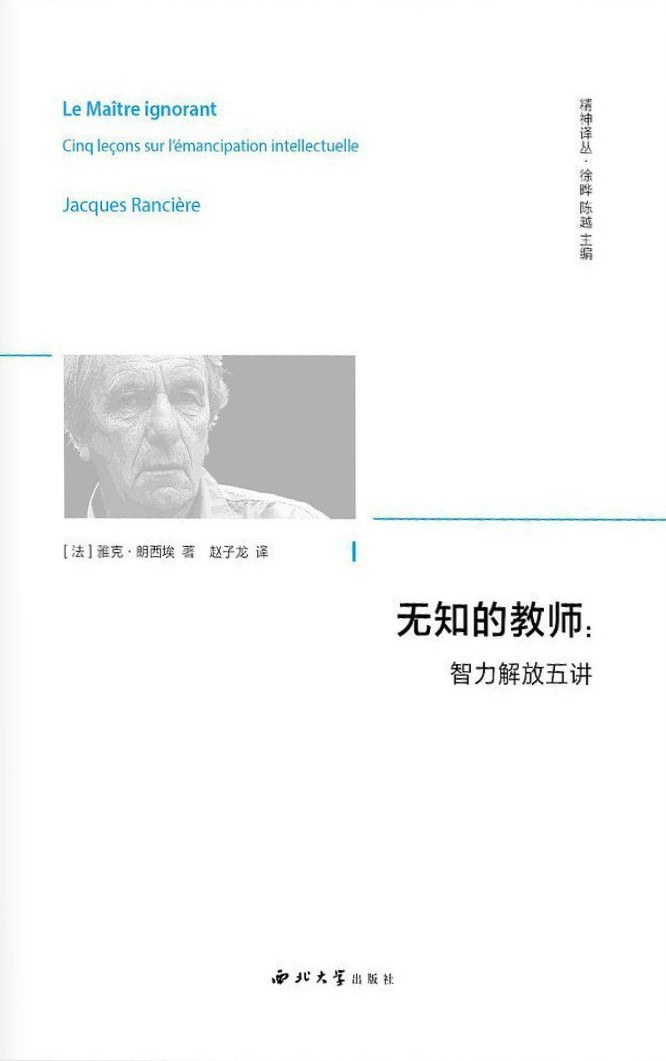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20-1
界面文化:如果作为分享者的文学教师所能吸引到的只是原本就具有天赋、能够被感召的一小部分人。在这个意义上,你会觉得文学教育的实用性被大打折扣吗?
张秋子:我觉得整个大学的文科教育都和使用性无关,它是一种悬置,截停或者说推迟了学生们去面对严峻社会的可能,让他们赢得了某种空想的、聊赖的空间。
本雅明说人文学科是给聊赖者准备的。这种聊赖不是贫乏无聊,而是一种心境上的闲散。他做了一个特别好的比喻,说聊赖的感觉像一条外表看起来灰色的针织围巾,而围巾的内部是丝绸的、五颜六色的内衬,在我们做梦的时候,是五颜六色的那一面包裹着我们。
文科的大学的四年,就是被这个内衬包裹的四年。尽管最后我们可能都必须要面对生存的困境,但我们至少拥有了四年喘息和做梦的空间。而绝大多数人在工作以后,是不会做梦,甚至厌弃和鄙夷做梦的。
人们变得越来越难处理“光晕”,只能处理清晰、直给的东西
界面文化:你在书中提到细读是一项需要引导和训练的技艺。你是否观察到当今读者更青睐于细节少、情节性强的作品?这是一种现代的阅读习惯吗,它是被什么塑造的?
张秋子:确实,像这些年流行的非虚构,就是更倾向于去报道故事情节,而不是通过细节来塑造人。但这其实并不是什么很新的东西,人对情节具有本能的强烈癖好。只不过和情节相比,文学故事,或者我们所说的小说,它和叙事的手法紧密相关。
在我看来,叙事手法赋予了情节本雅明语境中的“光晕”,它让情节包裹上了一层不透明的东西,不能马上被解释,需要读者进行更复杂的思考。被短视频之类荼毒已深的现代人可能确实相对欠缺这种思考的心理机制,人们变得越来越难处理“光晕”,只能处理清晰、直给的东西。
界面文化:最近几年,互联网上许多读者出于女性主义的视角,将那些刻板塑造女性、含有性暴力内容的作品称作“老登文学”。一些网友指出“老登文学”这样的标签遮蔽了文学选材和写作的复杂性,另一部分则认为披露文学作品中的“老登”元素是一种公共性的女性主义行动。你如何看待这样的阅读方式?
张秋子:在现实需求导向下,我理解这种阅读方式的价值。对文学作品中厌女和暴力元素的强调,确实会让我们意识到,社会中存在这样的事情,需要我们去正视,而不能无视或美化它。
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阅读方式本身不应该径直走向对文本的否定。文本写作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如果用现在的眼光去约束一切历史中的文本,很多文本就没有办法读了。最典型的像《荷马史诗》中,战争是海伦作为一个叛逃者和在男人之间被挑选者诱发的。
如果我们完全按照意识形态化的角度来解读的话,这样的作品可能都会受到否定。意识形态化的角度很容易去走向那种概念性的解释。比如说陀氏的时间观是如何反映了基督教的时间观,会一下子跳到很宏观的地方。

在课堂上,我们也经常涉及女性主义话题。比如讲到易卜生的《玩偶之家》的时候,谈到娜拉这一反抗夫权的形象,我会引导大家问他们谁支持自己的妻子当全职太太,以及为什么。但我不会在学生面前显露出我的立场来,我不希望引导或要求他们反什么或者站什么。我对意识形态引导的警惕可能也和前面说到的对于启蒙的警惕有关系。
界面文化:你觉得当AI文本和人类文本并置时,识别文本的原创性和人类性是困难的吗?
张秋子: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希望首先强调我不赞成太依赖“原创性”来判定作品的优劣。以莎士比亚来说,他在他所处的时代被称为乌鸦,因为乌鸦会把其他鸟身上的羽毛粘在自己身上。当你去看莎剧,你会发现莎剧是无所不抄的。但是他在抄的过程中,又注入他自己独特的能量和魅力。
所以我们可能需要用一种更加宽容的角度来理原创性。原创性不是写以前从来没有人写过的东西,而是指在前人模仿前人基础上,放手让自己施展出我的天赋和我的能力的过程。过于强调原创性,其实是在放大人的无限性,当我们意识到每个人其实都是有限的、每个个体都要接触无数他者的时候,我们才能完成自我的塑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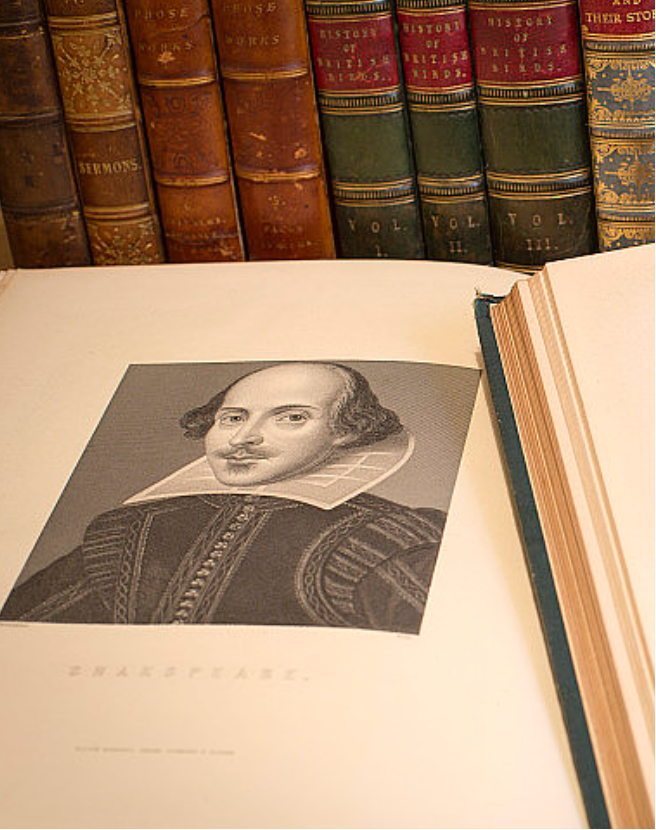
界面文化:这让人联想到之前的鉴抄事件。有相似立场的说法是,任何文学写作都有模仿和学习的过程。但是如果创作者尚且处于需要大量模仿的过程中,就不应该着急把作品发表出来。
张秋子:是的,我也反对逐字逐句的抄袭,但鉴抄事件更像一个导火索,指向的是我们对于社会不公的某种发泄。在内卷的语境中,大家都不满于在社会资源贫瘠的状况下抄袭者可以如此招摇过市,这个才是根源。
原创性问题说到这里。回到你提出来的“人类性”,我认为好的作者能够把他们真实的生命经验组织成有生命重重回响的文字,而AI可以去编经验,却无法令那些经验打动人。因为那些经验往往过于完美、没有瑕疵。
今天路上我听阿黛尔的歌,听的是一个现场版,发现她有一句唱走调了,我第一反应是这里不好听,第二反应是这不是录音棚里面那种完美的歌,恰恰因为那一句走调,让我感觉到了阿黛尔的血肉状态。AI文本的光整其实有一些油腻。人在接受光整的东西的时候往往一下子就理解了,没有惊跃(surprise joy)的过程,没有刺痛的感受。但人类的表达常常让人愣一下,让人不解为什么要写这个、要这样写,这种摩擦力能唤起读者与写作者智识的博弈,让阅读变得更富启发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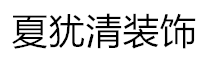











 京ICP备2025104030号-12
京ICP备2025104030号-12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